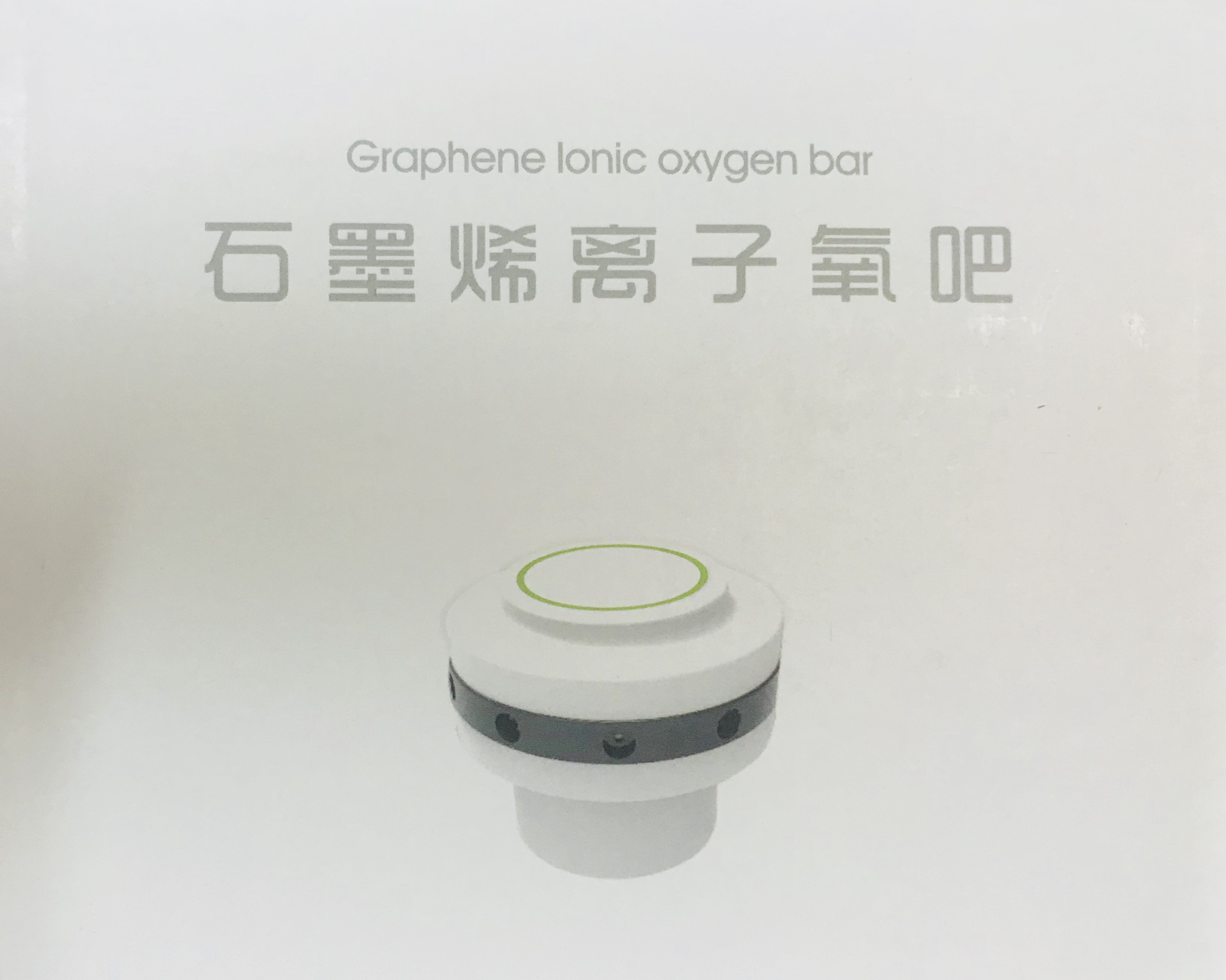当个“数字游民”,怎么样
时间:2023-10-09 22:51:26 作者:我的信息
光明网评论员:“4年走遍20个国家,95后女孩裸辞成为‘数字游民’”——今日华西都市报的报道,再次将“数字游民”这一概念带到人们眼前。
“数字游民”,是指过着数字游牧生活的人,最初源于新千年左右一本名为《Digital Nomad》(数字游牧)的书。书中论述了一个观点:“技术可能会让社会回归游牧的生活方式”。华西都市报这篇“数字游民”报道的主人公,是一位旅游博主,本来是辞职旅行,结果“辞职旅行”却最终成为了新工作,目前在各个社交平台已经有了两百万的粉丝。
游民这个词很有意思,表征一种超出定居定点生活的状态。互联网技术打破了以工厂、公司为主要单位的工作场景,解构了那种流水线串联起来的封闭空间,似乎让更多“打工人”奔逐到了自由广袤、水草丰美的地方。尤其是,这种状态是生活与工作一体的,审美与谋生一体的,似乎消解了工厂、公司场景下分工对生活的异化,何其动人。因此在招聘平台的调研报告中,76.4%的00后愿意成为“数字游民”,2022年全球“数字游民”已经达到3500万人。
不得不说,和这个庞大的意愿相比,“数字游民”提供的可能只是一条狭窄的通道。游民前面有“数字”二字,已经标定了这个概念是基于技术媒介存在,而技术并不中性,本质上是由资本驱动的。技术媒介展现的是资本的高阶逻辑,流量让资本加速流动、热搜不断创造着资本变现的时刻,一个要在这当中谋生的人,其实要遵守更为严苛的资本增殖逻辑,比如粉丝量、转化率、外链数量,以及各个平台不同而繁琐的推量规则。这些,各平台的博主、网红、UP主、KOL已经深有体会。打破了工厂和公司的边界,媒介生存者仍然处于一个封闭的资本空间中,只不过,KPI的评价规则不同了,是更大的自由承诺之下的高阶绩效管理。
今天报道“数字游民”的主人公是以视频、照片为主产品的旅游博主,她对目前工作的感受是“对人的自觉性要求很高”,“有时候看到一个好看的东西,第一反应是一定要拍下来,哪怕心里是不想拍的,身体还是会驱使自己拍下来,这是另一种无形的约束,也是一种‘职业病’。”这个真实的体会,也传递了技术媒介对“游民”潜在的训练和要求。2012年,Facebook(脸书)几乎是以一种急迫的态度收购以图片照片为展示形态的Instagram(照片墙),提出的价格超过后者双倍的市值。这在当时曾被包括Facebook高管在内的很多人的不理解,直到人们很快发现,这个收购是以“互动率达到Facebook10倍”“广告营收贡献率占比超过50%”为指向的。如果要在这样的平台上谋求数字资产的积累,那么必须要遵循它的系统增殖逻辑,无论你的照片和视觉产品是什么审美。
如果仅讲择业,“数字游民”肯定是一个新的选择,新的机会。如果在择业上增加自由向度,甚至寄寓诗与远方的希望,估计它不免会让向往者失望。数字技术常常带来自由错觉,尤其在互联网普及早期的时候,也许现在,更应该看到它控制性的一面。
(转载请注明来源“光明网”,作者“光明网评论员”)